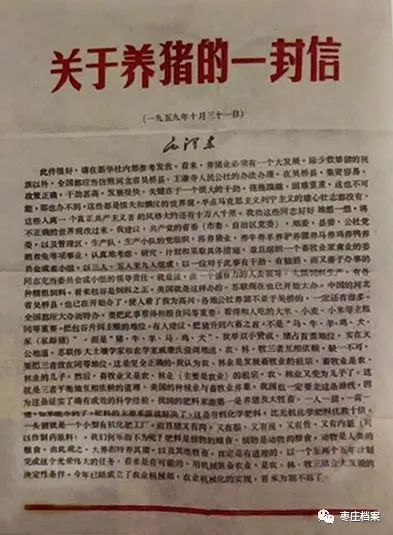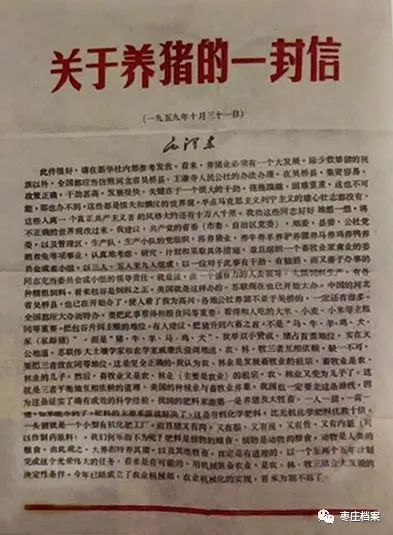1959年10月,毛主席号召“大养其猪”,开启一个恢宏的养猪时代,社员老百姓几乎家家养猪,支援国家建设,有条件的生产队也要养上几头,这一直延续了近三十年。历史上传统的“六畜”,指“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犬、豕(猪)”,猪的地位比狗低,20世纪60年代以后,猪蹿升于六畜之首,成了“猪、牛、羊、马、鸡、犬”,狗则排在了末位。其时有宣传语曰:猪全身都是宝;又曰:一头猪就是一座小的肥料厂。

为了鼓励社员养猪,政府还制作了直观形象的张贴画,画面上,一头肥猪被肢解得七零八碎,然后用箭头线和图画标示:猪肉可以作副食,猪鬃可以做毛刷,猪皮可以做皮革,猪骨可以做骨胶,猪油可以做肥皂,最后,猪粪可以当肥料等。无须猪“自我标榜”,单凭这幅画,就足以使那些东游西走、无所事事的狗子们汗颜,自愧弗如。“文革”时期彩色故事片《青松岭》里的反面人物钱广有句“著名”台词:“吃粮靠集体,花钱还得靠自己”。电影里的钱广作为群众中的落后分子,是在宣传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。但抛开电影的政治意涵,平心而论,钱广的话在当年是有其合理性的。

那个年代,猪不仅是农村百姓家里的重要“成员”,还是家庭财富的重要象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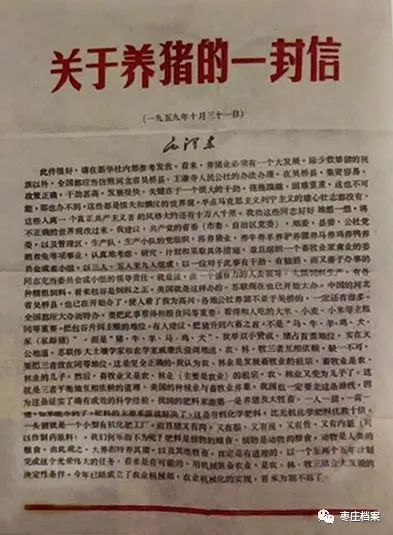
当时的农业社只是初步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,个别盲目追求高指标多交公粮的生产队,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好,成了所谓的“高产穷队”。一个劳动力工一日只值几毛钱,社员花销开支,除在自留地上种点经济作物换点钱,余下就是指望养猪养羊了。看一个农户过不过日子,陈实不陈实,养猪是一个重要的“考核”指标。一个农家如果养着两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,主人腰杆都挺得“是直”(方言“直溜”的意思)说话都有底气。猪就是家庭开支的希望所在,就是大把的人民币。那个时候口粮紧张,但“分槽养马,合槽喂猪”,多头猪,可以互相竞争吃食,养两头猪的居多。老百姓的农家院,除堂屋、厨房、茅厕外,再狭小,也要垒个猪圈,不会想到养猪散发的臭味是否影响人居环境和身体健康。喂猪的饲料,都是“绿色”的,没有所谓的添加剂、瘦肉精。猪的生长速度也似乎很慢,大致要喂养一年左右才可以出栏。而猪的“待遇”比现在也好,吃熟食。猪吃生玉米、生饲料,都是养猪场规模喂养以后的事了。我们那一带农村,晚上,等忙完了生产队的农活,放了工,家家户户冒烟,那不是烧晚饭,当年农村都是两顿饭,那是在生火拉风箱烀猪食。烀猪食的主要原料是碾碎的下脚料地瓜干——好的地瓜干要做口粮,如果是冬天,要加上浸泡后的干芋头叶,烀熟的猪食,散发出略带焦煳味的香甜气,如果饿了,连人也忍不住都想尝上一口。喂猪的时候,秋天还要掺鲜芋头叶,给猪催肥的时候,还要加碎豆饼,这样,猪可以吃得香,吃得多,长肉快。饱餐后的猪懒洋洋地躺在猪窝里晒太阳睡大觉,不必担心高血脂高血压,心无旁鹜地长膘、长壮、长肥。而狗子们的待遇要差远了,尽管模样比猪可爱,会摇尾巴看家护院,但由于创造不了多少价值,常常被忽视,偶尔偷吃猪食,还要受到主人的呵斥,惶惶不可终日。猪除了可以换钱外,一个重要功能,就是生产农家肥。猪圈里的猪粪,掺杂了泥水,经猪每天踩踏、“打腻”,时间一长发酵后,就是上好的圈肥,可以交给生产队换工分,工分多,分到的口粮才多,所以有人说“分,分,社员的命根儿”。但也有投机取巧者,平时命往猪圈填土,等到生产队收圈肥之前,用草木灰偷偷给圈肥上上色,增加圈肥的“品相”,好多卖工分。那个时候,国家实行计划经济。为了优先保证工业生产和军队、城市供应,对农副产品统购统销。所以,农户养的猪,不愁销路,猪养大了,由国有食品站负责收购。六七十年代,食品站毛猪收购价,根据猪的肥瘦及出肉率,一等六毛五一斤,二等六毛一斤,三等五毛五左右,同时还奖售平价饲料、化肥和布票等。

由于毛猪价格稳定,猪肉价格十几年一贯制,一直定在七毛三分钱一斤。往食品站卖猪,农户称为“号猪”。号猪这天,一般要给猪喂点好的猪食,但注意不能喂太饱,否则,猪吃饱以后肚子胀大,验级员会查验出来,影响猪的等级少卖钱。在猪的嚎叫声中,人们七手八脚把猪捆扎好,抬放到地排车上后,要赶紧拉着往食品站走,路上不要拖延,因为猪随时拉屎撒尿,这都是猪的“斤称”,一泡屎或一泡尿,意味着要“拉去”一两块钱。从食品站归来,农户拿着号猪得来的人民币,心里踏实多了,可以盘算着盖房子、儿娶女嫁、置办新式家具等事项了。当然,更不会忘记及时“补栏”:过不了几天,就会有一两头“奶憨子”(仔猪)出现在空荡荡的猪圈里。“铁打的猪圈流水的猪”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几乎每个农家都在重复上演着同样的故事。当今时代,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,就吃的意义讲,可以说人人都是“肉者食”,尽管一段时间以来猪肉涨价不少,但只要想吃,花上个百儿八十,到超市里买上几斤,就可以做顿红烧肉大快朵颐。只是,不知道是平时吃“好东西”把味蕾整麻木了,还是猪肉的品质下降了,总是感觉肉的口味不如过去偶尔吃顿好了……
参考馆内文献:
《薛城文史》之田园牧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