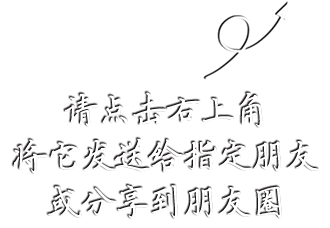台网互动
随笔《市南工业区杂忆——瘦肉换板油》
2014-04-23
老家有个李姓邻居在枣庄市肉联厂工作,天天骑着自行车吱吱嘎嘎地来回,他也是邻居们最喜欢议论的一个人物,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在肉联厂工作。那时候每个家庭吃油用半斤的小瓶装,谁家要用脸盆盛油,将是了不起的生活条件。议论李邻居的主要原因说他人长得精瘦,不到一百斤的感觉。大家说肉联厂是什么单位啊,是个大肉铺子,到处都是煮好的肉,顶风十里能闻到那厂里的香味。有人又说,可能是里面的肉不随便吃,管得严,要不李邻居瘦成那样?也有人说李邻居天天在那里习惯了,什么肉都吃够了,什么肉也都不想吃了,所以就这么瘦。于是大家都替李邻居感到亏的慌,几个小伙伴发狠,说要是把我放到肉联厂里面,——哼! 放暑假的时候,我真的跟着父亲去了肉联厂,好像是去找那个李邻居卖肉,肉买的不多,价格不让秤上让了些,但数量也不足够解馋。去的路上我一直调整嗅觉,集中精力,心想先用鼻子去闻闻香味解解馋,可到了肉联厂大门口也没闻到一丝香味,相反是一阵阵热风裹着一股股臭烘烘的气味飘来,直钻鼻孔。父亲知道了我的心思后,笑说肉联厂不煮肉,是杀猪的地方,哪来的香味? 再转脸看看墙外的水沟旁,依次蹲了几个人,都在用铁笊篱打捞飘来的碎油块。肉联厂的确很大,大到里面还通火车,大到火车装了一列车猪肉顺着铁路不知到了哪里。父亲说肉联厂杀猪不用刀,用电。后来我在各塔埠食品站里见过,果然是用电。见师傅们先把猪从圈里赶出来,肥猪哼哼地从单行道依次到来,师傅摸起一个电烙铁样子的东西,扯扯拉拉对准肥猪的耳根部,猛地一戳,只听得肥猪嗷的一声,应声倒地,然后再放血剥皮,开膛破肚,最后肢解分类。那时的猪下货说下等东西,往往三毛五毛一斤,两块钱足可装一化肥袋子。源于父亲与肉联厂食品站几位朋友感情甚笃,常常在自行车后面,捆一袋子或猪蹄大肠或猪头肝肺回家,所以我家也经常是猪油几盆,冬天挺硬却雪白,夏天白里透软黄。 父亲自从和肉联厂食品站的私人关系建立以后,也从此开始忙碌起来,张家出殡办场,李家儿娶女嫁,无不请他帮忙卖肉,买来后打开一看,见是肥瘦均匀的五花,都称感谢,带来一个后腿,一看全是瘦肉,主家会眉头一皱,然后再强作笑脸,勉强口谢。若能买来的一堆白花花的板油,主家则满脸是嘴,霎时喜笑颜开,一串嘿嘿之后,才想起掏烟道谢。 这些年,父亲在老家每年都喂两头猪的,体重都在四、五百斤,牛犊一般大小,在春节前杀了,一头卖掉,一头留着过年。猪膘很厚,膘油白的喜人看着吓人,心里却想去吃。瘦肉当然金贵,更金贵的当然是父亲的一年辛苦和良苦用心。喂猪全用粮食和青草,杀了以后又分割给亲友,然后把两套猪下货留着煮了,节后让我和弟弟把朋友请来吃肉。大家对吃肉当然没什么稀罕,但这种以瘦当肥或以肥当瘦的口感,大家都没设什么顾虑,一时间肉吃满腮酒喝大碗,豪爽之气油然而生。 昨天又去了肉联厂,虽然得知早在1996年就已停产,但看到铁轨仍有新痕,冷库门口有工人装卸货物,不是成匹的猪肉,也没闻到曾经的热风臭味,这说明肉联厂死了,其部分器官还有生命,就像我老家庙里的那棵千年柏树,枯了身子,仍有几枝残存绿意。就想了,肉联厂与其这样苟延残喘,倒不如尽快重获新生,让崭新的聚艺谷在肉联厂这块土地上肥肥成长起来,来唤起人们对他过去的肥瘦记忆。
同类新闻
-
161星期前
-
94个月前
-
114个月前
-
134个月前
-
94个月前
-
94个月前